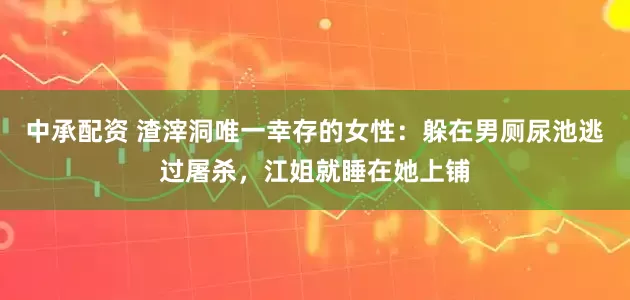
游中相被捕时,特务从他住处搜出一个笔记本。
本子应该烧掉的,来不及了,上面写着三个垫江女中教师的名字:傅伯雍、陈鼎华、盛国玉。
1948年10月的那个下午,盛国玉正在桂阳小学给女教师们讲课。
她说的不是课本上的内容,而是些关于新社会、新生活的想法。
这是丈夫余梓成交给她的任务——用教师身份作掩护,做些思想工作。
特务冲进来时,她正在黑板上写字。
没有反抗,没有逃跑的机会。她被押上卡车,连家都没回。
展开剩余94%车子开出垫江县城时,她回头看了一眼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。
审讯室的灯很亮,照得人睁不开眼。
特务问她认不认识游中相,她说见过几次。
又问她做过什么,她说只是教书。他们不信,用电击。
电流通过身体的那一刻,盛国玉昏了过去。醒来时全身剧痛,嘴里全是血腥味。
她确实什么都不知道。
余梓成是地下党员,从不在家里谈工作上的事。
1947年经人介绍结婚后,盛国玉只是觉得丈夫常常早出晚归,偶尔让她帮忙传个话、送个东西。
她以为自己只是做些边缘的小事,没想到这些"小事",已经够她被关进渣滓洞的理由。
从垫江到重庆,一百多公里山路。
车子在歌乐山脚下停住,眼前是一片黑黢黢的洞口。
这里原本是个小煤窑,因为渣多煤少,当地人叫它渣滓洞。
1939年军统特务霸占了煤窑,改成了集中营。三面环山,一面临沟,想逃出去几乎不可能。
盛国玉被推进女牢二室时,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。
空气里弥漫着霉味和血腥味,她找了个角落坐下,双手抱膝,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距离组织批准她入党,还差两个月。
现在这两个月,变成了永远无法跨越的距离。
牢房里有人在低声说话,有人在哭。
盛国玉什么都没说,只是盯着墙上的裂缝发呆。
那天晚上,她第一次睡在渣滓洞的木板床上,硬得硌人,冷得刺骨。
上下铺之间的托扶床是上下铺,盛国玉住下铺,上铺的女人很瘦,身高只有一米四五,走路一瘸一拐。
她用化名叫江雪琴,但牢房里的人都叫她江姐。
第一次见面时,江姐刚被提审回来。两个特务架着她,她的脚几乎不沾地。
回到牢房后,她靠墙坐了很久,一动不动。
盛国玉看见她的手指红肿得像胡萝卜,十个指头上都是血痕。
那是竹签扎过的痕迹。
江姐负责过联络工作,掌握着重庆地下党的名单和联络方式。
特务对她用尽了酷刑:戴重镣、坐老虎凳、吊鸭儿浮水、夹手指。
在一次次审讯中,她昏死过三次,但从没说出一个名字。
到了晚上要睡觉,江姐准备爬上铺。
她的手指已经无法用力,只能用手腕吃力地勾住扶手,身体一点点往上挪。
盛国玉看着,忍不住站起来,托着江姐的腰往上推。
江姐回头看她,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从那天起,这成了每晚的固定动作。
盛国玉推,江姐爬,有时候江姐身上的伤太重,盛国玉推得很小心,生怕碰到伤口。
推的时候,盛国玉常常会哭,眼泪滴在手背上,也滴在江姐的衣服上。
同室还有几个人,杨汉秀是军阀杨森的侄女,但她不认同伯父的所作所为,选择了另一条路。
因为这层特殊关系,特务对她稍微客气些,她也借此为牢房里的人争取一些便利。
胡芳玉话不多,总是坐在角落里。左绍英年纪大些,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着年轻的姑娘们。
彭灿碧有个习惯,喜欢对着墙壁小声唱歌。
彭灿碧
夜里特务不许讲话。
但江姐和盛国玉会敲床板,或者把手伸下来,拉一拉对方的手。
不需要说什么,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。
有时候是鼓励,有时候是安慰,有时候只是想确认对方还活着。
江姐向狱医要来了红药水和处方签,用来写字。
她每天用红药水在处方签背面写《新民主主义论》提纲,字很小,密密麻麻。
还组织牢房里的人学习,讨论怎么和敌人斗争。
每当有人被提审,其他人就自发地唱歌,为即将受刑的人助威,一直唱到她回来。
歌声在牢房里回荡,盖过了外面的脚步声。
1949年10月,胜利的消息传进来了。
那天晚上,江姐提议:"同志们,我们给新中国缝一面国旗吧。"
大家找来藏起来的红布和黄纸,按照报纸上"五星红旗"这个名字,凭想象做了一面旗子。
她们不知道五颗星该怎么排列,就把大星放在中间,四颗小星围在四周。
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很轻,每个人都听得见。
那面旗帜很粗糙,但在昏暗的牢房里,它是唯一明亮的东西。
盛国玉参与了缝制,她的针脚不太整齐,她一针一针缝得很认真。
她想,如果有一天能出去,一定要看看真正的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。
11月14日的镜子那天早上,特务的脚步声比平时急促。
"江雪琴!"
牢门被打开,特务站在门口,手里拿着名单。"还有李青林,收拾东西,要转移了。"
整个牢房突然安静下来。
大家都知道"转移"意味着什么。
江姐站起来,很平静,没有慌张,也没有挣扎,脱下囚服,换上自己的衣服,那是件灰色的布衫,洗得发白但很整洁。
然后她围上一条白围巾,动作很慢,像是在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约会。
"盛国玉,把你的镜子借我用一下。"
盛国玉把小镜子递过去,手在发抖,江姐接过镜子,认真地照了照,用手拢了拢头发。
她的手指还是肿的,梳头时很费力,还是坚持把每一缕头发都整理好。
江姐转身,一个一个地和大家告别,握手,拥抱,或者只是对视一眼。
轮到盛国玉时,江姐拍了拍她的肩膀:"就要解放了,一定要斗争到底。"
盛国玉扶着江姐走到牢门口。
走廊很长,光线很暗,国玉和其他人把手伸出栅栏,拼命地挥手。
江姐回头,冲她们笑了笑,然后转身上了车。车子开走了,扬起一片尘土。
下午,血腥味从电台岚垭方向飘过来。
很浓,很刺鼻,牢房里的人都闻到了,谁也没说话,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江姐牺牲了,年仅29岁。
从那天起,渣滓洞变得更加压抑,不再放风,每天只准两个人出去倒尿罐。
特务的巡视变得频繁,办公室的灯整夜亮着。
牢房里的人们挤在一起,小声讨论着外面的局势。
11月27日,天气变冷了,还下着秋雨。
但从牢房里能听到南岸传来的炮声,那是解放军的炮声,一声接一声,像敲鼓一样有节奏。
大家都很兴奋,觉得解放就在眼前了,也许明天,也许后天,就能出去了。
盛国玉靠在墙上,听着外面的雨声和炮声。
她想起江姐说的那句话:"就要解放了。"是啊,就要解放了。
她想,如果江姐能多等几天,多等十几天,就能看到新中国,看到重庆解放,看到五星红旗真正的样子。
可是江姐没能等到。
那天晚上,牢房里的人们唱了一会儿歌,扭了一阵秧歌,取暖,也给自己打气,天太冷了,大家很早就睡下了。
盛国玉躺在下铺,看着上面空荡荡的床板,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她没想到,这一觉醒来,会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。
尿池里的二十小时深夜,脚步声,"起来!起来!办移交了!"特务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,每个牢房的门都被打开。
两间女牢的人被驱赶到楼下八室,二十多个女人,还有两个女婴,一个叫卓娅,一个叫苏菲娅。
盛国玉站在靠近后窗的位置,鼻子里闻到浓重的汽油味,心跳得很快。
一声哨响。
机枪从门窗伸进来,火舌喷出,子弹像雨点一样扫射。
盛国玉顺势倒在后窗左角的架子床边,身边有人倒下,有人尖叫,有人高喊。
那是胡其芬的声音,很快就被枪声淹没了。
枪声停了,脚步声靠近。
两个特务推开门,对着满地的尸体又是一阵扫射,盛国玉趴着不动,连呼吸都尽量放轻。
一个特务走到她身边,用枪托在她腰上戳了几下,很疼,她咬着牙一动不动。
特务嘟囔了一句什么,转身走了。
门被锁上,然后是火光。
汽油被点燃,火势很快蔓延开来,盛国玉被浓烟呛醒,牢门已经烧倒了,楼板上冒着火星,马上就要塌下来。
她想,反正都是死,不如冲出去,站起来,冲出牢房,跳过两堆燃烧的火。
院子里没有特务,他们已经撤了,盛国玉猫着腰,钻进最近的男厕所,趴进尿池。
尿池里又脏又臭,还有别的男同志也躲在里面。
她把脸埋在臂弯里,不敢出声,不敢动,甚至不敢想接下来会怎样。
外面的火光映红了天空,哭喊声、倒塌声、爆裂声混在一起。
她又晕了过去,不知道过了多久,天亮了。
11月28日清晨,附近二十一兵工厂的家属,看到渣滓洞火光冲天,跑来查看,发现了昏迷的盛国玉。
她们冒着危险把她抬出来,送到老乡家里藏起来。
盛国玉发着高烧,在山上又躲了两天。
11月30日,她听到有人在喊:"重庆解放了!重庆解放了!"她才敢下山,才敢相信自己真的活下来了。
渣滓洞180人遇难,15人脱险,盛国玉是唯一的女性。
盛国玉活了下来,带着江姐的嘱托,带着那些牺牲者的记忆。
1996年,70岁的她终于入党,完成了48年前的愿望。
2014年7月27日,88岁的她安详离世。
她用一生记住了那个寒冷的深夜,记住了上下铺之间的托扶,记住了镜子里江姐整理头发的样子,也记住了尿池里那二十个小时的黑暗。
发布于:河南省顺阳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